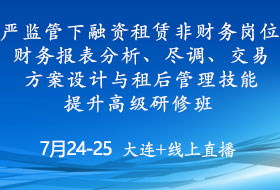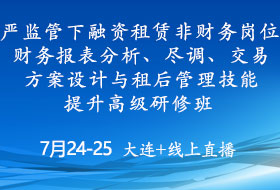融资租赁公司要远离地方政府融资市场“陷坑”
2016年5月,也就是一年之前,因融资租赁的地方政府扶持政策的讨论,笔者曾顺带针对融资租赁的“地方政府融资”市场进行了分析。
在对一种可能的新型地方政府融资手法进行描述的同时,也基于地方政府融资租赁扶持政策推出的政治与经济背景分析,得出了中央政府的监管反制随时可能“出手”的判断。所以,在文章的结尾处,笔者给出了一个发问:“也许,另一场饕餮的盛宴已经准备就绪,只是,在席间,不知道中央政府是否会猛然推门而入,令许多甜蜜的富贵梦,破碎一地?”
随后,中央政府果然不出意料地“猛然推门而入”了:2016年10月,财政部因接到“举报”而启动对贵州省各级财政违规担保的撤销工作;2017年1月,财政部因审计提供“线索”,而发函五省份、两部委,建议问责包括重庆黔江区教委回租赁合同在内的,数起地方政府的违规举债行为;2017年3月,重庆黔江区财政局长被行政撤职;2017年4月26日,在金融“监管风暴”全面发动的背景下,财政部、发改委、司法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六部委,联名发出“财预[2017]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50号文”)。
从“50号文”开篇就强调的,“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融资担保行为摸底排查”工作,要在“2017年7月31日前清理整改到位”,逾期不改正或改正不到位的,“应当提请省级政府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的严厉要求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容忍度,已经迫近底线。
在如此的新形势下,包括融资租赁公司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应该如何看待“地方政府融资”市场,是一个值得被深入讨论的话题。
一、地方政府融资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
从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经营角度,讨论新形势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与“地方政府融资市场”中的“机会”和“风险”,必须首先建立起一种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关系的深刻认识。
“中央-地方”关系问题,是一个“超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即,无论古今中外,但凡一个国家的疆域充分广阔,都会产生这个问题,也必然要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历史上,“王室与诸侯”、“皇帝与郡县”、“朝廷与府县”都是这层关系的具体表现,而新中国成立后,就体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1978年改革启动之前,虽然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权限,有过数次的下放尝试,但都因“一放就乱”而随即改回。所以,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总体而言,处于一种依照各种指令执行的完全被动地位。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尤其是改革重心在1980年代中期,由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地方政府就成为中央政府推动和落实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就体现为一种明显“鼓励”态度下的“放权”——深圳特区的建设以及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都是对这种“中央-地方”关系的现实印证。
然而,伴随着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自我意识”的逐步强化,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意识”也随之而起。代表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与代表局部利益,甚至参杂个人私利地方政府,开始出现利益分歧。1993年,地方政府凭借对银行资金的调度力量,通过房产开发商而迅速堆积放大的“海南地产泡沫”,成为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在改革启动后首次“角力”的导火索。经此一役,中央政府切断了地方政府染指“银行资金”的权力,并通过“分税制”改革,重新规范“中央-地方”关系——这就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状态的形成起点。
失去了“银根”的地方政府,略一沉吟,便将目光投向了“地根”。地方政府依靠“地根”提供资源支持,催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送地生税”,也即以“开发区”为载体,通过大幅压缩土地对价,换取“招商引资”,并依此构建厚实税源;第二阶段是“卖地换钱”,也即众所周知的“土地财政”;第三个阶段则是“押地融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设立,就是“押地融资”阶段的起点和最鲜明特征。那时,正是2008年前后,次贷危机让中国已然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循环的,带有显著“外向型”特征的经济系统,面临“失速”的危险。为了维系整体经济安全,中央政府的“四万亿”强刺激投资计划即时推出。
然而,投资计划的执行,离不开投资主体的存在。所以,通过建立“地方融资平台”,重新打通银行资金向地方政府的流动,就成为中央政府的不得不为之的一项措施安排。于是,恍惚之间,昔日重现,地方政府再次拉上了银行的手。有统计称,截至2010年底,就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供设立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其中省级165家,市级1648家,县级4763家。也正是如此迅猛成立的平台融资公司,成为“十万亿”信贷投放的重要推手,然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就此萌生。
很显然,地方政府并不满足于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单一地获取银行信贷资金。
中国资本市场失范演变推动之下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地方融资平台的举动,令地方政府“恍然大悟”:这个“公司组织”形式出现地方融资平台,就像是地方政府手中的一个“电线插头”,既然这个插头可以“接入”银行体系,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去“接入”资本市场?
乃至更进一步地,为什么不通过设立地方的国有“金控平台”而主动“进入”金融市场?于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与地方政府开始产生破坏性“共振”:资金资源被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输入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此自然不会坐视不管:2014年发布“43号文”并启动地方债务置换,2015年启动实施新《预算法》,2016年“营改增”全面铺开,直至2017年的“50号文”和金融“监管风暴”。
综上,很明显地,“地方政府融资”在中国是一个十足的新事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只是“地方政府融资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还包括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金融手段,以各种地方国有企业或公益事业组织及设施(教育、医疗、供水排污等)为载体,直接从银行体系,或者间接通过资本市场以及融资租赁“通道”从银行体系获取资金的种种举动。
二、地方政府融资市场: “供需”禁锢,“支点”抽离
本文开篇处所列举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融资的种种“遏制”,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临时性举动。得出这一论断,其分析基础在于对又一组重大关系的考察——“政府-市场”关系。
界定“政府-市场”关系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相对而言,经济系统运行所需的资源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更加有效,还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指令或行政干预更加有效?这个问题在中国改革的早期,被非常凝练而通俗地表述为:“找市场,还是找市长?”。
虽然,有人仍然把历经近40年改革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称为“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但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地位,却毫无疑义地呈现出一种压倒性地上升趋势:从中央政府的历年重大政策文件措辞看,对“市场”的表述,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对“市场”作用的定位,也从“基础性”上升到了“决定性”。
随着“市场”地位的不断隆升,“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地位,当然就会表现出相对下降。但是,这种政府地位的相对下降,绝对不会退变为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主张的“守夜人”角色,引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表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即,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需要发生转变,这就是“转变政府职能”。
那么,政府的职能要发生怎样的转变呢?从政府对经济影响和作用看,政府要从“管理者”,转变为“治理者”——如果把经济运行比喻为一场交响音乐会的话,“管理者”向“治理者”的转变,就要求政府从过往动手“谱曲”,甚至亲自“演奏”的角色,转变为交响乐的“指挥”角色,以及音乐厅“老板”的会场运营维护角色。
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功能与分工看,相当一部分“事权”,将会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如是表述:“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所以,如果将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力度比喻为一块“蛋糕”的话,那么,不但这块蛋糕将变得的越来越小,而且,地方政府在这块蛋糕上的分配比例,也将变得越来越低。
既然地方政府的角色将要发生这样的变化,那么,地方政府融资市场在趋势上,自然会变得空间受限。如果要对“受限”进行具体描述的话,从已经发生的种种现实状况看,可以将之称为:“供需”禁锢,“支点”抽离。
在地方政府融资市场的“需求端”,地方政府融资的规模和方式,都已经被非常严格地固定下来。“50号文”再次重申了“国发[2014]43号文”的规定:“地方政府举债一律采取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并且,针对地方政府融资的各类“通道”融资手段,“50号文”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方式,要求或决定企业为政府举债或变相为政府举债”。
但是,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考虑,“50号文”特别表达了对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化”手段,参与金融活动的支持:“允许地方政府结合财力可能设立或参股担保公司(含各类融资担保基金公司),构建市场化运作的融资担保体系,鼓励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依法依规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地方政府依法在出资范围内对担保公司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意图通过其他路径“曲线”进行融资的意图,也被叫停:“地方政府不得以借贷资金出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
在地方政府融资市场的“供给端”,2017年春季发动金融“监管风暴”,首先以“资产要‘穿透’,资金要“寻源””的原则要求,给各类金融机构套上了“紧箍咒”。而“50号文”则遥相呼应地给出了,触发“紧箍咒”的具体条件:“金融机构应当严格规范融资管理,切实加强风险识别和防范,落实企业举债准入条件,按商业化原则履行相关程序,审慎评估举债人财务能力和还款来源。金融机构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提供融资时,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担保”。实际上,金融机构在操作地方政府融资业务时,如此注重地方政府的“担保”态度,正是金融机构的狡黠之处。
因为,各类金融机构都非常清醒地知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罢,地方政府融资市场也罢,其偿债的主要现金流来源,并不是一般概念中,可以类比为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财政收入”,而恰恰是地方政府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地方政府的举债空间。
而所谓的各种担保形式,无非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满足金融机构内部风控的“形式合规”,让投放决策有能有一个好看的“面子”,一旦出了问题,无论是管理层还是信审人员也都能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托词”;二是增加地方政府的违约成本,提高自身债权在地方政府偿债序列中排序位置,毕竟,在相当程度上,地方政府同各类金融机构已经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生”关系,一旦金融机构“翻脸”发难,伤及地方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信用”,也是地方政府所难以接受的状况。
所以,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在地方政府融资市场“供给端”的禁锢手段,是最为有力的控制手段——如果说,因违规举债而对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予以撤职,颇为不妥的话,那么,因违规放债而对金融机构的最高管理者予以撤职,则是水到渠成的当然之举。所以,“50号文”中对于金融机构的问责规定,才是真正的“大杀器”:“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提供担保承诺的,依法依规追究金融机构及其相关负责人和授信审批人员责任”。
在粘合地方政府融资市场“供需”两端的“信用支点”方面,“地方政府担保”早在“国发[2014]43号文”中,就已经被“抽离”:“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违法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而“50号文”则又打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补丁”:“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参与PPP项目、设立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损失,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方承诺最低收益,不得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等任何股权投资方式额外附加条款变相举债”。
那么,“地方政府担保”的信用支点被抽离后,还存在有其他的“信用支点”吗?理论上,是有的——也即举债企业或举债融资平台企业自身的“信用”。但是,在相当程度上,这也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支点”。“50号文”号召:“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尽快转型为市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这一号召本身就暗示着,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过往一贯所开展的,并非“市场化融资”,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具备自身本有的“信用支点”。
更进一步地,“50号文”还非常明确地抽离了几项非常具体的,地方政府向融资平台公司提供“信用支点”的具体形式:“地方政府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储备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承诺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入作为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不得利用政府性资源干预金融机构正常经营行为”。
三、远离地方政府融资市场“陷坑”
尽管,从“政府-市场”关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关系,乃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举债和金融机构经营的规范和监管动作,都非常清晰而有力地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市场将愈发空间局促,且风险叵测,但是,“装睡的人叫不醒”,部分金融中介的投机欲望,以及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固有的,“掌柜”坑“东家”的“代理人问题”,乃至各种新式“变通手法”所引致的侥幸心理,还是会触发一些地方政府习惯性的“融资冲动”。换言之,市场中依然还会存在一股力量,妄图“抵抗”趋势。
那么,这些“抵抗”力量的胜算如何呢?
在地方政府融资市场中,逆势而动的那股力量能否“得手”,与中央政府对全局监督与控制能力高度相关。也即,中央政府的监督与控制能力越强,在地方政府融资市场中“唱反调”的胜算就越低。
从已有的现实状况看,最高决策层以及中央政府所拥有的监督与控制手段,日趋丰富。除了上文已经表述的种种政策手段之外,最高决策层以及中央政府还拥有以下“利器”:
1、与“党建”和“廉政”相配套的纪检监督和司法监督:“巡视组”和检察机构当然可以将地方政府举债相关事宜,纳入工作范围;
2、金融监管:2017年以来,证监会频出“顶格”罚单,银监会在掀起“监管风暴”的同时,还强调要进行“强问责”,而保监会在项俊波落马后的监管动作也愈发凌厉;
3、舆论与新闻监督:习大大曾数次强调:“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从笔者切身的体会来看,习大大这柄“尚方宝剑”还是威力十足的:曾有所谓“公关公司”就某篇公众号文章而联系笔者,笔者把这段话“摆”出来后,对方就此悄然无声。另外,近日“财新”媒体以《穿透安邦魔术》一文来P.K.“安邦保险”,也是非常好的例证;
4、信息监督:李克强总理在《2017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形成全国统一政务服务平台”,可以想象,一旦这个全国的政府信息系统形成,将及时而有效地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力度;
5、人大监督:“人大监督”也是习大大非常重视的一项举措,这一领域的“潜力”很大,来自于各级人大及其委员会的监督,很有可能象“民主生活会”、“巡视回头看”一样,成为一种更加有力的机制性的常设监督手段;
6、依法行政:一旦“法治”取代了“法制”,检察和司法机关逐步消除“地方化”特征,党领导下的独立的司法体系,将形成对政府行政的有力规范——2017年5月4日,习大大考察北京政法大学,绝非随意为之。此外,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根据计划,《行政监察法》将修改为《国家监察法》,并拟于2017年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据此而论,只要不出现类似次贷危机这样的,难以预测的重大系统性冲击事件,进而导致已有的地方政府融资市场“供需”禁锢和“支点”抽离各种手段的力度减弱,只要种种着眼全局的诸多监督控制举措持续推进——依照上文的分析,这些都将是大概率事件——那么,任何地方政府融资市场中的“抵抗”力量,前途终是暗淡。
并且,因“抵抗”大势而招致的“苦果”,也必将难以下咽:除非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能够真正依靠“市场化”的审慎风险识别能力,来涉入地方融资平台市场或地方政府融资市场,否则,来自于供需两端的禁锢力量,以及因“信用支点”抽离所导致的风险敞口,足以让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遭受重创。
即使从“个人利益”出发,延续过往“通道”式的监管套利手法,也颇为不智:一个运营投机套利和简单中介业务的职业经理人,将因此而丧失宝贵的管理实践机会,也很可能因潜在的巨大经营隐患而断送自己的未来职业前途;一个仅会“对接项目”的“非标”业务操作人员,将因此而蹉跎职场的黄金岁月,让自己拎着一幅单薄的“金融民工”身板儿,去面对转眼即至的中年危机;即便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领导成员,也将难逃干系:根据2017年5月3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6号文”),“党建”的力量将结合公司治理手段,在2020年前的短短不到3年时间内,深度融入包括金融行业在内的全体国有企业。
由此看来,对于包括融资租赁公司在内的各金融机构而言,明智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走“市场化”路线,依靠真正的企业管理能力来开发地方政府融资市场;第二条路就是,另寻出路,远离地方政府融资市场“陷坑”——一如巴菲特在2017年的股东信中所言:“‘其他人都在做,所以我们也必须做’的观点,在任何行业都造成了麻烦”。
来源:怀邦咨询,作者/ 李喆
上一篇:融资租赁与传统租赁的差异
下一篇:船舶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能否美梦成真